儒学的佛学化与道教化
2014/9/6 热度:173
南朝儒学从总体上说,大体与东晋相同,儒家学者承魏晋玄学之余绪,或绝经世之志而兴厌世之思,或斥儒道佛无益于天下而耽于酒色,或痛骂仁义礼法之不足用而寄托于老庄之虚无,玄学盛行,清谈成风。儒学界通行王注《周易》、杜注《左传》、何注《公羊爪学间清通简要》。唐李延寿所撰《北史·儒林传》对南朝儒学总评道:”自元嘉之后,宇内分崩,礼乐文章,扫地将尽。……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且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阿洛,《左传》则服子镇,《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筒,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这大体可说明南北学术之差别及南方学术的基本学风。 南朝儒者长于文笔,又濡染于玄谈佛理,重文辞,轻经术,故其说经之文多空虚浮华,这是南朝儒学的总体特色。但是具体而言,南朝四代儒学,至少可分为两大阶段,两阶段的基本情况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第一阶段主要是宋、齐时期。这一时期从官方的情况看,儒学的地位并没有下降,依然是诸学之首,依然担负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角色。但是,由于玄、史、文学的分割,儒学明显丧失一家独霸的地位,并与诸学平分秋色。《资治通鉴》南朝宋元嘉十五年载:“豫章雷次宗好学,隐居庐山。尝征为散骑侍郎,不就。是岁,以赴士征至建康,为开馆于鸡笼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艺文,使丹杨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并次宗儒学为四学。”以致具有传统儒学观念的司马光不无感慨而言之:”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于此可知儒学地位在南朝前期确有所下降,而不久前兴起的玄学则脱离儒学自成一家。 宋、齐时期儒学地位的下降为历史事实,然考诸此时儒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却发现《礼》学格外兴隆,大家辈出,著述繁富,远非他朝可比。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写道:”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宋初雷次宗最著,与郑君齐名,有雷、郑之称。当崇尚老、庄之时,而说礼谨严,引证详实,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究其原因,盖与政治混乱过程中如何重建社会秩序有着一定的关联,也多少反映出儒学在此一时期虽然地位下降,但其功能犹在。 然而到了南朝儒学的第二个阶段,即梁、陈时期,由于梁武帝公开宣布儒、释、道三教并行,三教合流的趋势更为明显,当然也为此后隋唐时代儒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南史·儒林传》在描述梁、陈时期儒学状况及其背景时说:”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功课末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至梁武创业,深悯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场补博士,备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馈票,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笼者云会矣。又选学生遣就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撒,分道博十、祭酒,到州都立学。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业,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陈武创业,时经丧乱,衣冠珍瘁,寇贼未宁,敦奖之方,所未逞也。天嘉以后,稍置半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其所采缀,盖亦梁之遗儒。” 也就是说,在整个南朝时期,儒学除在梁武带的扶持下有过短暂的辉煌外,基本上都因政治环境的恶劣而萎靡不振。政治环境对于学术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干戈未息、政治动荡不安的年代,不可能指望学术的真正繁荣。而且从南朝政治、学术的总体形势看,由于儒、道、释三家的不断争夺与冲突,为政治对文化的选择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在南朝诸帝中,除梁武帝有意识地扶持过儒学外,其他帝王则更多地是信仰佛教和道教,这也是南朝儒学一直衰微的原因之所在。 梁武帝以政权的力量平息了神灭与神不灭之间的争论,但是如果从思想史的观点看,无疑是以范缜为代表的儒学理性主义在理论上占了上风,更多一些道理。同时,由于这场争论的双方往往都引用早期儒家经典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因而这场争论的实际后果是谁都没有取得真正胜利,反而因这场争论促进了儒佛在思想上的融合。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开启以儒释佛、儒佛互让的学术思潮。他们一方面将儒家思想引入佛教义理,促进佛学的中国化和儒教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将佛教的一些思想引入儒学,使传统儒学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不得不发生一些本质性的变化,从而为后来的儒佛合一作了理论上的铺垫和准备。刘宋时”兼内外之学”的名僧慧琳在其所著《均善论》中,便是坚守佛教的立场而同时主张儒释道三教调和,以为三教的刨始人均是圣人,三教的义理亦各有长处,应该调和,应以善”。梁人刘勰所著《灭惑论》也说:”夫佛家之孝,所苞盖远。理由乎心,无系于发,若爱发弃心,何取于孝?”明确承认佛教义理不仅不违反传统儒家的孝道,而且与儒家的孝道相互发明,”夫孝理至极,道俗同贯,虽内外迹殊,而种用一撰。”其孝道的原理与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尽管二者存有内外之别。 以儒释佛、佛儒互证在南朝的另外一种表现形态是把儒家一些理论融入佛理,以期由此证明佛教义理不仅不妨碍儒教的推行,而且会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梁和尚僧顺著有《释三破论》便强调佛教教义中自有仁义忠孝之道,只是表现形式不一,但其功用则相同,”释氏之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大和妻柔,各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产基于这样的认识,南朝儒释之间的冲突尽管激烈,但相互吸引与融合则是最为本质的东西,当时学者不论是站在儒家,还是佛教的立场上,他们都逐渐承认二教之间确乎有相通相融之处,二者应该携起手来,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于是南朝儒佛在思想上融合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宣扬三教同源,功能则一,力主三教并用。 确实,就人类文化的初期形态而言,各种文化形态尽管存在许许多多的特征和差异,但它们之所发生的根本原因当然只能是人们的精神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儒释通三教同源,而且可能人类文化的所有形态都是起源于此一背景。问题在于,儒佛之间经过几百年的冲突,到了南朝突然发现二者同源,便使人不能不觉得这是二者冲突过程中的相互容忍和让步。梁武帝萧衍在大力弘扬儒教的同时,并不废儒、道三教,尤倡儒学;采取”孔释兼弘”,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大体可以说明南朝统治者及一般士人和僧人对三教关系的基本态度,由此亦可知他们论证三教同源的根本目的。 儒道合一在东晋之前还只是某些思想的沟通与融汇,儒家学者真正从儒学的立场走上道教的立场,还是从东晋的葛洪开始。据葛洪《抱朴子》”自叙”,他早年也是儒家学术的忠实信徒,”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孤陋寡闻,明浅思短,大义多所不通。但贪广览,于众书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既性暗善忘,又少文,意志不专,所识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纯儒,不中为传儒之师。”由此可见,他之所以抛弃儒学而转向道家,并不仅仅出于个人爱好,而是时代和社会思潮使然。这一方面反映了儒家文化僵化与式微的一般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新起的道教确实存在吸引人的东西。正如其在《抱朴子》“序”中所说:”道士渊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难,又无可咨间。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为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举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谓之妖妄之说见余此书,不特大笑之,又将谤毁真正。”足见其对道家”长生之理”的倾心以及对传统儒学的厌恶。 儒道互补、内外双修是葛洪的理想;怎样才能真正弥合儒道之间素来存在的理论冲突,则是这一理想能否实现的关键。为此,葛洪将儒家伦理引入道家的思想系统,有效地解决了早期道家与道教欲达到修炼的目的而掘绝人间事务的矛盾。他在《对俗》篇中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样一来,便将道教追求肉体成仙和精神解脱与儒家在现实生活中追求理想的道德境界的内在冲突基本调和,对后来的儒道合一、三教合流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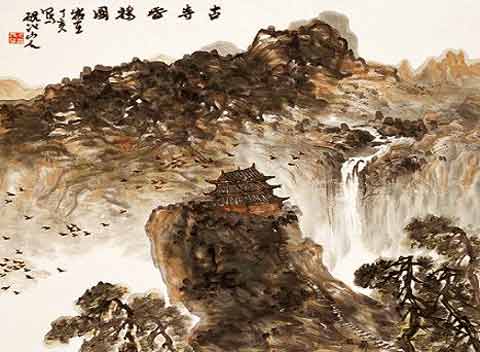

电脑上扫描,微信中长按二维码,添加地藏菩萨平台公众号
五明学习: 五福文摘: 佛教入门 | 历史传记 | 身心灵 | 生活艺术 | 人与自然 | 人文杂话 | 其它 | 素食起步 |